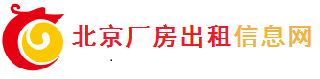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:产业园区的创新驱动和内源式增长
一
20世纪50年代以来,原料地对产业区位的吸引力减小,企业选址的自由度加大,招商引资为主的园区随自由布局型产业(Footloose industry)的出现而兴起。当生产环节在地理上分离,甚至可以跨洋散布;当富余资本满天飞,寻找降落地点的时候,园区战争就开始了。欠发达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渴望金凤凰的到来,对园区开发尤为积极。印制精美的宣传册、令人炫目的视频、LED屏幕、网络平台,园区广告铺天盖地。
据说全国从事专业招商的人数不下两万。招商的金句是:只要肯招商,没有挖不动的企业。通过各种招商术,很多园区招到世界500强,乃至港商、台商、粤商、温商,还能以商招商,园区像滚雪球一样长大。但是不少园区苦苦经营了十来年,却难以维持,企业就是不到那儿去。
如果把园区看成装载企业的容器,那么打造园区是地产商的事。然而,对于肩负促进地方振兴使命的地方政府来说,引资不是为政绩,是要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负责任的。企业是长脚的,会跳的,大型企业还会及时调整空间战略,有投资,也有撤资。因此打造园区是有风险的政策措施,园区存在失败或空洞化的危险。
二
解释产业园区的理论之一是增长极理论。2017年我和学生李鹏飞为国际地理百科全书撰写的“增长极和增长中心”条目发表,我从理论上对园区失败现象进行过思考。
20世纪50年代初期,法国学者佩鲁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不平衡,把抽象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,把其中的推动性单位描述成增长极。1960年代中期,学者们进行推论,使增长极学说从一种推动性产业促使其他产业增长,演变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促使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。
期待相关的经济活动在推动性单位的附近地区发展,通常是许多园区规划的设定目标。现实中有许多地方可供企业选择,决策者的期望可能不切实际。多年来学者们反思了地理空间的增长极学说:一定会在周边地区引起经济活动吗?如果推动性单位是一组公司,为什么这些公司会在增长极集聚?为此,必须补充集聚经济理论予以支撑,解释公共服务和专业化供应商的发展、对消费者的吸引、劳动力市场的共享,以及思想和技术的交流等。
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,在未经严格审查、激烈辩论和足够证据之时,增长极就已作为区域战略被多国广泛接受,盲目地假定增长极所引导的经济增长会自动发生。地方经济结构被认为是可以规划出来的。政策分析仅限于产业链投入-产出的贸易联系静态方面,而不包括企业间关系,例如社会互动和创新的溢出效应等非贸易联系的动态方面。
之后,一些增长极未能实现其初衷而被决策者放弃。增长极政策失败,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它被用于过度雄心勃勃的目标,如平衡国家的经济空间格局;在要求不高的地方经济中所建的增长极也未必能成功地带来发展;还有很多原因,例如维持这些政策的资源不足、政府换届使承诺无法兑现、增长中心或推进性产业的错误选择等等。
重要的是,内源性增长过程被排除在增长极理论之外。佩鲁和他的弟子们虽然强调了创新的单位对经济增长的意义,但把这些单位具有先进技术作为既成事实。而且,增长极的经济分析是非地方化的(“delocalized”)。增长极理论不能解释创新活动的发展,也无法解释推动性活动如何产生。自然,它暗示欠发达地区不能自行实现增长,而必须依靠增长极的引导。实际上,增长极战略的实施重点通常是在非创新的地区。该政策的制定者通常专注于产业链的投入-产出关系,只偏爱大型企业,不重视对创新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。
增长极在政策中的普遍应用无助于该概念的巩固。模糊的定义使本来只是解释不均衡增长的增长极理论,成为许多地区发展规划的论断、信仰和灵丹妙药,一种理论在证据巩固之前被广泛接受和作为政策来实施,这是非常危险的。
三
中国千千万万个园区令人眼花缭乱。20世纪70年代末建的小开发区已经“旧改”,而新时代的新城和园区方兴未艾。世界各国的园区与中国园区的情况大同小异,不过发展阶段千差万别。早在21世纪的矿山——信息技术、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初现端倪时,世界到处浮现高技术幻影,20世纪50年代中期涌现的“硅谷热”,迄今仍在继续。20多年前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向我叙述阿德莱德多功能城(Multifunction Polis of Adelaide,简称MFP)的梦想。近日我在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公司(APO)的网站上看到阿德莱德生物中心(Bio Hub Adelaide)即将在2021年3月启动的新闻。阿德莱德是南澳乃至南半球的新药研究和临床试验的热土,已建有生物医药城(Adelaide BioMed City)。我感到好奇的是,过去闹得沸沸扬扬的MFP现在怎么没有消息了。
MFP是1987年澳大利亚霍克(Hawke)执政时期,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的规模庞大而雄心勃勃的项目,当时计划在阿德莱德市中心以北8公里处的吉尔曼建设新世界概念的美丽城市。澳大利亚-日本问题评论家曾说MFP是个流动无形的幻影。烧钱多年,总耗资1亿澳元,即使削减成本的基廷(Keating)政府也不敢放弃它。但是很不幸,1994年股市崩盘、经济衰退,这座空中城堡的梦想破灭,1996年联邦政府撤资,1997年8月南澳州州长宣布放弃该项目。

图片来源:《悉尼先驱晨报》网站截图
三
用现在的前沿规划思想来看日本通产省1987年所提出的MFP概念,发现它不无道理。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1982年《大趋势——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》中就提到了高技术等于高接触(high tech = high touch),日本人很早就关联了高技术和高频率接触。在MFP规划时,澳大利亚人期待高技术城市的出现,日本人则考虑建造高频率接触的城市,双方从一开始就有误解,造成多年难以置信的管理混乱。当然,MFP的失败还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。
高技术和高接触并非矛盾,因为高技术的创新需要企业之间、产学研之间协同作用的创新环境。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,如传统工艺、时装业和高技术产业而言,技术与艺术难以严格区分,技艺改进需要他人的合作和响应。创新和学习成为集体行为,知识隐含于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,分工细化的人们需要频繁交流,创新在同业甚至跨界的知识溢出中产生。
在世界上,另外两个同样是打造了多年、曾经备受争议的产业园区,现在都成功了。一个是1968年设计、1972年开发、在法国戛纳和尼斯之间出现的索菲亚-安蒂波里斯,它是法国增长极政策时所挑选创建的增长极之一;另一个是卡图哈科技园,选址于西班牙相对落后的安达露西亚省、一度衰落的塞维利亚市,它是利用1992年世博会会址、通过周密规划设计和公共投资而培植出来的。2022年国际科技园协会(IASP)的世界大会将在卡图哈科技园举行。
四
那么,园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?关键是园区持续升级,走内源式增长和创新驱动之路。
曾经依靠外源式增长的加工区,经过20-30年的持续制度创新,会形成创新型的产业社区。世界第一个出口加工区——爱尔兰香农出口加工区,以及炸响“改革开放第一炮”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就是这样变身的。园区的内源性增长来自官产学研等行为主体的协同作用,为此,需要创造鼓励技术知识自由交流、根植于地方社会文化的制度环境。
创新并不一定发生在年轻的新区里。世界上最普通的创新环境,尤其是早期的创新环境,一直是位于大都市中心的。无论是老城还是新区,发生创新的地方都存在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网络。当代,创新型企业向生活环境好且空间尺度相对较小的城市街区集聚。精心设计的城市空间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催化剂。商务会议、工作交流、休闲交谈等,可以增加知识工作者之间的社会互动。咖啡馆、餐馆和广场等公共空间成为社交互动、企业间合作、观点交流和扩展办公空间的物理场所。